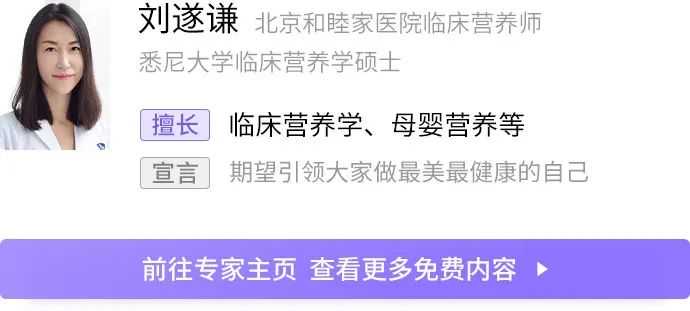《归途迷途》
"背上这伤疤是怎么回事?"我抚摸着妻子背上那道狰狞的疤痕,嗓子发紧。
她挣脱我的怀抱,慌忙拉上睡衣,转身时脸上闪过一丝慌乱。
"没什么,不小心摔的。"她低声说,眼神躲闪着我的目光。
1995年初春,我从广州外派归来。那是个微凉的夜晚,北方的春风还带着几分寒意,仿佛在提醒我这里不是南方。
我拖着行李箱走过熟悉的大杨树街,满眼都是三年未见的家乡风景。路边的水泥电线杆上,依旧贴着几张已经泛黄的电影宣传单,《飞来的女婿》、《红高粱》,字迹模糊了大半。
街口老李的自行车铺还亮着昏黄的灯光,他戴着那副裂了缝的老花镜,正低头修着车胎。
"哎哟,老周回来啦!"老李抬头瞥见我,放下手里的扳手,呲着那口掉了两颗的黄牙,"可算回来了!嫂子这三年没白等,成天盼着你回来呢。"
"是啊,终于回来了。"我笑着点头,心里却泛起一阵酸楚。
"快回去吧,别让嫂子等急了。"老李摆摆手,又低头忙活起来。
我加快了脚步,行李箱的轮子在坑洼不平的石板路上发出"哐当哐当"的响声。沿路的水泥矮房,砖红色的单元楼,屋顶上林立的电视天线,一切都那么熟悉又陌生。
记忆里的家,是个有着红砖墙的单元楼,五楼不装电梯,每次爬楼都累得气喘吁吁,但窗台上摆着她养的几盆吊兰,总让我觉得再累也值得。
三年前那个冬天,我接到南方厂子技术支援的任务。那时改革开放的浪潮正席卷全国,南方沿海城市日新月异,而我们这样的北方内陆小城,还守着计划经济的旧影子。
"好机会啊,老周!"厂长拍着我的肩膀说,"咱们厂就属你技术最好,去了好好干,回来就提你当技术科长!"
临行前,她站在火车站台上,手里攥着我给她照的那张黑白照,眼眶红红的不说话。照片上的她,穿着那件带着小碎花的蓝布衬衫,站在单位门口的花坛边,腼腆地笑着。
"你放心去。"最后她只说了这一句,却饱含千言万语。
火车开动时,她举起手使劲挥着,直到看不见她的身影。
想到这里,我的脚步不由自主地加快了。五楼,爬上去时我已经呼吸急促,但心却比任何时候都要热切。
推开家门,屋里饭菜香气扑面而来。老旧的木地板发出熟悉的"吱呀"声,墙上的挂钟还是那个黑色圆盘,时针分针走过无数个日日夜夜。
客厅的茶几上放着一台十四寸的"熊猫"牌彩电,比我走时那台黑白的"飞跃"牌要新得多。茶几边上是那个布满划痕的实木沙发,坐垫还是那套枣红色的,只是颜色比记忆中的暗淡许多。
桌上摆着我爱吃的地三鲜、红烧肉和凉拌黄瓜,旁边还有一小碟腌萝卜,那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开胃小菜。
宋秀芝站在厨房门口,围着那条我们结婚时买的碎花围裙,微微笑着。她比三年前瘦了,眼角添了几道细纹,穿着那件已经洗得有些褪色的蓝色毛衣,头发还是那样整齐地挽在脑后。
可那双眼睛依旧明亮如初,像是北方冬天的星空,沉静而有光芒。
"回来了。"她轻声说,声音有些颤抖。
"回来了。"我放下行李,一步跨过去将她搂进怀里。
她的身体微微发抖,我能感觉到她在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这就是我的妻子,从不轻易在我面前流泪,总是把那份柔软藏在刚强的外表下。
"吃饭吧,都凉了。"她轻轻推开我,转身去拿筷子。
"好香啊,三年没吃到你做的菜,我都馋坏了。"我笑着说,想要缓解那份突如其来的情绪。
"少贫嘴,南方那么多好吃的,能把你馋着?"她嗔怪道,但眼里全是笑意。
饭桌上,我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好像我只是出差几天回来,而不是离别三年。她问我南方的工作,问我那边的天气,问我有没有学会说广东话。我问她单位的情况,问她父母的身体,问邻居家的孩子有没有考上大学。
我们就这样默契地避开了那些深沉的思念和牵挂,仿佛只要不说出来,那份苦涩就不存在一样。
吃完饭,我从行李箱里拿出给她带的礼物——一条南方特产的真丝围巾,一瓶据说很补的木瓜膏,还有一个精致的小风铃。
"这是什么?"她好奇地拿起风铃。
"广州的一个老师傅做的,说是能招来好运气。"我解释道,"你看,风一吹就会响,声音很好听。"
她小心翼翼地挂在了窗前,微风吹过,风铃发出清脆的响声,在这个简朴的家里平添了几分诗意。
"真好听。"她笑着说,眼睛亮晶晶的,像个得到心爱玩具的孩子。
夜深时,我们相拥而眠。这张老旧的木床还是我们结婚时买的,躺上去会发出轻微的"咯吱"声。窗外偶尔传来几声狗叫,远处电线杆上的广播喇叭早已安静。
我的手无意间触到她背上那道疤,心头猛地一惊。这三年来,她每月都会寄来一封信,信纸上是她那整齐却略显生硬的字迹,讲述着家里的琐事,单位的变化,却从未提过受伤的事。
"这疤怎么回事?"我又问了一遍,声音里带着不容回避的坚持。
她沉默了片刻,伸手关了台灯。
"不小心摔的。"黑暗中,她的声音轻如蚊蚋,"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没再追问,但心里却如同打翻了五味瓶。那道疤痕粗糙而狰狞,绝不是普通的摔伤可以解释的。
她为什么不愿告诉我?这三年里还有多少事情被她藏在了只言片语之外?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我就醒了。南方的生活让我习惯了早起,而此时的北方还沉浸在黎明前的寂静中。
宋秀芝已经起床,厨房里传来锅碗瓢盆的声音。我悄悄起床,走到客厅,发现茶几抽屉没关严,里面露出一角红色的本子。
鬼使神差地,我拉开抽屉,拿出那本磨损严重的笔记本。翻开第一页,上面工整地写着"宋秀芝工作笔记",下面是1992年的日期,正是我离开的那年。
本子里记录着她每天的工作内容,偶尔夹杂着一些家务事的备忘。最后几页,我看到一张剪报,是去年《纺织工人报》的一则简短报道,标题是《我厂宋秀芝同志勇救落难工友》。
报道简短地描述了一起事故:去年冬天,纺织厂传送带突发故障,一名女工衣服被卷进设备,危在旦夕,宋秀芝不顾个人安危将其救出,自己背部严重受伤……
我的手微微发抖,胸口像被一块大石头压着。多少个日日夜夜,我在南方忙碌时,她瞒着我经历了这样的磨难?
看着那些字迹,我仿佛看到她独自一人在医院的病床上,咬牙忍痛,却在给我的信里只字不提,只问我过得好不好,工作累不累。
"起这么早?"她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我慌忙合上本子,却已经来不及了。
她站在门口,手里端着刚出锅的小米粥,脸上的表情有些尴尬。
"为什么不告诉我?"我举起那张剪报,声音哽咽。
她放下粥碗,走过来坐在我身边,轻轻叹了口气。
"有什么好说的?一点小伤,哪里值得惊动你。"她的声音平静,就像在谈论今天的天气一样。
"小伤?"我几乎要喊出来,"你差点伤到脊椎!"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她抬起头,眼中带着我熟悉的固执,"你在南方忙大事,我不想你分心。"
我沉默了,心中五味杂陈。是啊,这就是我的妻子,宁愿自己咬牙承受,也不愿给别人添麻烦的宋秀芝。
"我今天要去你单位看看。"吃过早饭,我决定道。
"去干嘛?"她警觉地问。
"看望老同事,顺便了解一下情况。"我没有明说,但她知道我指的是什么。
她没再阻拦,只是低头整理着桌上的碗筷,好像那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
我去了她工作的纺织厂。这是个建于六十年代的老厂,红砖高墙,大门上方的"跃进纺织厂"几个大字已经褪色。门卫室的玻璃窗上贴着几张黄纸,写着"安全生产""质量第一"的标语。
"周工!"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我转身看到了以前的同事老王,他现在是厂保卫科的干事。
"老王!好久不见!"我和他热情地握手。
"听说你这次回来就不走了?"他笑着问。
"是啊,南方的活干完了,组织上让我回来。"我点点头。
"你媳妇可是咱们厂的宝贝疙瘩。"老王压低声音说,"去年那事,没跟你说吧?"
我摇摇头:"一个字都没提。"
"典型的宋秀芝作风!"老王苦笑,"你不知道啊,评先进的时候,车间主任非让她上台领奖,她就是不去,说救人是应该的,不值得表扬。"
看门的老刘大爷从门卫室探出头来,叼着烟卷向我招手:"来看嫂子啊?你媳妇没跟你说啊?去年救了小赵一命,差点自己出事。全厂都传遍了,就您不知道。"
我心头一震,脚步不由得沉重起来。
厂区里,机器轰鸣,棉絮漂浮在空气中。高大的纺织机旁,工人们忙碌着,脸上或多或少都带着疲惫。这景象我再熟悉不过,三年前,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我找到了车间主任徐大姐,她比三年前胖了些,头上的白发也多了,但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还是那么锐利。
"老周回来了!"她热情地拍着我的肩膀,"南方混得怎么样?学到真本事没有?"
"马马虎虎吧。"我笑着回答,"徐姐,我想问问我媳妇的事。"
她的表情立刻严肃起来,拉着我到角落里,压低声音说:"那天传送带出了故障,小赵的衣服被卷进去,眼看人就要被带进去,秀芝扑过去拽住了她,自己却被带子划伤了后背,差点伤到脊椎。"
"送医院时,血把衣服都浸透了。"徐大姐的眼圈红了,"医生说再晚一点,可能就瘫了。你媳妇躺在病床上,疼得直冒汗,却还关心着小赵,问人家有没有事。"
"她在医院躺了多久?"我哽咽着问。
"半个月。后来硬撑着回来上班,说是家里一个人闲着也是闲着。"徐大姐摇摇头,"我们都劝她多休息,她不听,说是干活反而不觉得疼。"
"她怎么一个字都没跟我提?"我艰难地问道,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你在外地,她怕你担心呗。后来评先进,她都不愿意上台领奖,说什么那不算啥,谁都会那么做。"徐大姐拍拍我的肩膀,"周工,你媳妇是个好样的。咱们这一代人,哪有不负重的日子?但像她这样硬扛的,真不多见。"
我说不出话来,心里既是心疼又是自责。这三年,我在南方忙着技术攻关,每天和各种仪器打交道,以为自己做了多大贡献,可是妻子在这平凡岗位上的默默坚守,那份无声的勇敢,才是真正的坚韧。
"对了,你去看看小赵吧,三车间的。"徐大姐指了指走廊尽头,"那姑娘一直想当面谢谢你呢。"
三车间比一车间安静许多,机器声不那么震耳欲聋。工人们三三两两地忙碌着,空气中飘荡着棉纱的气味。
小赵是个二十出头的姑娘,圆脸蛋,扎着马尾辫,见到我来,立刻放下手中的活计跑过来。
"周大哥!"她亲切地叫道,脸上带着腼腆的笑容,"嫂子说您今天回来!"
"你好,小赵。"我点点头,"听说去年多亏了我媳妇。"
提起这事,小赵的眼圈立刻红了:"要不是嫂子,我现在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她指了指墙角的传送带,"就是那里,我衣角被卷进去,整个人都要被带进机器了,嫂子冲过来拉住我,自己却被带子划伤了后背。"
"最可怕的是,她当时就疼得脸色发白,却还安慰我说'没事,小伤'。"小赵擦了擦眼角,"后来听医生说,如果伤口再深一点,可能就伤到脊椎了。"
我心里一沉,想象着妻子忍痛的样子,心如刀绞。
"嫂子住院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去看她。"小赵继续说道,"她从不提自己的伤,反而教我织毛衣,说是要织条围巾送您。后来我学会了,她说您喜欢蓝色,所以我也织了一条。"
说着,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手织的小围巾,蓝色的,针脚整齐,一看就是初学者的作品。
"嫂子教我织的,说是您快回来了,让我赶紧学会送您。"小赵把围巾塞到我手里,"嫂子受伤那阵子,还总念叨您,说您在南方辛苦,不能让您担心。"
我接过围巾,手指不自觉地颤抖。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家"。不是遥远的期盼,不是虚无的承诺,而是这样踏实的牵挂与守候。
"谢谢你,小赵。"我声音哽咽,感到一种深深的愧疚,"我我都不知道"
"嫂子就是这样,总替别人着想。"小赵笑了,"您是嫂子的骄傲,她总说您在南方做大事呢!"
回家路上,我在小卖部买了瓶二锅头。这是本地产的酒,粗糙但率真,就像我们这座小城的人一样。三年来,我习惯了南方的细腻,却也怀念北方的粗犷。
天色渐晚,路边的杨树在风中沙沙作响。对面的电线杆上,广播喇叭里传来《新闻联播》的声音,播报着遥远的国家大事。几个放学的孩子从我身边跑过,书包在身后欢快地晃动。
这是我的城市,也是我的根。不管走得多远,终究要回到这里,回到她的身边。
宋秀芝正在厨房忙活,听到我开门的声音,探出头来:"回来啦?饭快好了。"
我放下酒瓶,走进厨房,从背后轻轻抱住她。她的身体微微一僵,随即放松下来,手上却没停,继续切着案板上的青菜。
"去单位了?"她问,声音平静,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
"嗯。"我简短地回答,把脸埋在她的颈窝里,深深地呼吸着属于家的气息。
晚饭时,我给她倒了杯酒,她推辞:"我不会喝。"
她愣住了,随即垂下眼睛,像个做错事的孩子:"有啥好说的,不过是举手之劳。你在南方忙大事,我不想你分心。"
"可你差点出事啊!"我的声音不自觉提高,眼眶发热,"你知不知道我有多心疼?"
"我这不好好的吗?"她抬头,眼中带着倔强,"你那边压力那么大,我知道的。电话费贵,你也不常打,但每回听你声音都是疲惫的。家里这点事,我能应付。"
我一时语塞,心中百感交集。是啊,那三年,南方的生活看似光鲜,实则压力重重。多少个夜晚,我一个人躺在狭小的宿舍床上,听着外面不熟悉的方言,想着千里之外的她。
而这边,她独自熬过伤痛,却在每封信里只字不提,只问我吃得好不好,工作累不累。
"傻子。"我声音哽咽。
"你才傻。"她瞪我一眼,眼圈却红了,"我那天就想,要是出了事,可不能让你知道,不然你得多自责。"
"喝酒。"我举起杯子,不由分说地与她碰杯,"敬你,我的英雄。"
她被逗笑了,脸上泛起红晕,小心翼翼地啜了一口,立刻皱起眉头:"怪难喝的。"
"老李头前几天还问起你呢。"我故意转移话题,"说你这三年天天盼我回来。"
"胡说八道!"她立刻反驳,脸更红了,"我天天忙着呢,哪有空想你。"
"是吗?"我笑着逗她,"那小赵怎么说你教她织围巾,说是要送我?"
她一下子低下头,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那姑娘嘴真碎。"
夜深了,窗外的月光透过纱帘洒进来,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影子。我们躺在床上,她靠在我怀里,呼吸均匀而安稳。
我轻轻抚摸她背上的疤痕,那道伤疤已经结痂,但摸上去还是凹凸不平。在我的心里,这不是丑陋的伤痕,而是她的勋章,也是我们这代人的缩影——默默付出,不求回报。
"疼吗?"我轻声问。
"早不疼了。"她回答,语气里带着倔强。
"以后别瞒着我了,好吗?"我在她耳边轻声说,"我想和你一起承担,无论是喜悦还是痛苦。"
她靠在我怀里,沉默了一会儿,才轻轻点点头:"你也是,有啥难处说出来,咱俩一起扛。"
"我南方那个宿舍,连个像样的暖气都没有。"我开始讲述这三年从未对她说过的艰难,"冬天冷得要命,夏天又热得睡不着。饭菜不合口味,技术攻关又遇到瓶颈"
她安静地听着,时不时插上一句,偶尔笑出声来,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
"你呀,就是个倔驴。"她嗔怪道,语气里却满是疼爱,"早说不就得了?我寄点老干妈给你,热乎乎的,配米饭可香了。"
窗外,春风拂过大杨树的枝头,发出沙沙的响声。风铃被吹得轻轻晃动,发出清脆的声音。我知道,无论前路如何,我们已在彼此的港湾找到了归途。
第二天清晨,我早早起床,帮她做了顿早饭——虽然只是简单的鸡蛋面条,但她吃得津津有味,眼里满是笑意。
"你学会做饭啦?"她惊讶地问。
"在南方没办法,要么学会做饭,要么饿肚子。"我笑着回答。
"看来这三年没白去。"她得意地说,好像我的进步是她的功劳一样。
吃过早饭,我们一起去了她的单位。一路上,她挽着我的胳膊,像是怕我走丢一样。春日的阳光洒在她的脸上,映衬出细小的皱纹,却更显得温婉可亲。
厂里的同事看到我们,纷纷打招呼,眼神里带着善意的调侃。有人喊着"秀芝,你家周工回来了",有人问"老周,这次不走了吧?"。我们笑着一一回应,宋秀芝的脸一直红到了耳根。
下班后,我们去市场买了些新鲜的肉和蔬菜,准备晚上做顿丰盛的。路过文化宫,正好在放露天电影,是部老片子《牧马人》。
我们买了两张票,坐在后排的长椅上,肩并肩看着黑白的画面在幕布上晃动。影片里,主人公历经磨难,终于回到了家乡,回到了心爱的人身边。
"像不像我们?"我悄悄问她。
她"噗嗤"一声笑了:"人家是为了理想,你是被派去的,能一样吗?"
"都一样。"我认真地说,"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为了未来。"
她不再说话,只是轻轻靠在我的肩上,呼吸平稳而安心。
回家的路上,街上的霓虹灯一盏盏亮起,远处的工厂冒着袅袅白烟。这座城市在慢慢苏醒,准备迎接改革开放带来的新机遇。
我们的生活,也在这个春天重新开始。
晚上,她提出想听我讲南方的见闻。我便讲述着那里的高楼大厦,繁华的街道,各种新鲜的事物。她安静地听着,眼睛里闪烁着好奇和向往的光芒。
"等有机会,我带你去看看。"我许诺道。
"真的?"她像个孩子一样兴奋起来。
"当然是真的。"我握住她的手,"以后咱们哪儿也不分开了。"
她点点头,眼里闪着泪光。
入夜后,我轻轻抚摸她背上的疤痕,那是她的勋章,也是我们这代人的缩影——默默付出,不求回报。我想起了小赵的话,想起了徐大姐的评价,想起了这三年来她写给我的每一封信。
在这个普通的家庭里,在这个平凡的城市中,我的妻子用她的方式诠释着什么是真正的坚强和爱。而我,也终于明白了什么是归途,什么是家。
窗外,春风拂过大杨树的枝头,发出沙沙的响声。风铃被吹得轻轻晃动,发出清脆的声音,像是对我们未来生活的祝福。我轻轻吻了吻她的额头,在她耳边低语:"谢谢你,一直等我回来。"
她没有回答,只是更紧地依偎在我怀中,如同久别重逢的候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巢。
而我知道,无论前路如何,我们已在彼此的港湾找到了归途。那些曾经的迷途,都化作了今夜的星光,照亮我们携手前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