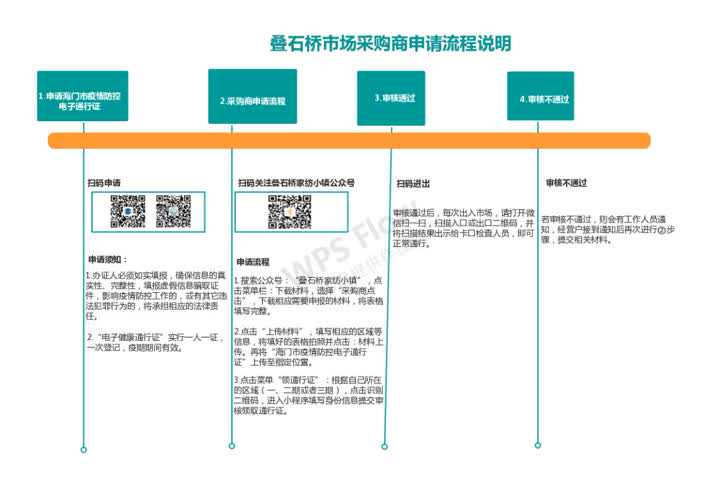正月初八那天,父亲突然收拾起行李,脸色凝重地说:"我要去新疆找你哥。"
这话如同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我心中无数涟漪。
哥哥和父亲,整整一年没说过一句话了。
我看着父亲粗糙的手指笨拙地折叠着那件已经穿了十多年的蓝色棉布中山装,心里泛起一阵酸楚。
那是1978年的夏天,一个闷热难耐的下午,我们家的老座钟刚敲过三点。
国营纺织厂要分房,按理说以哥哥的工龄和成家情况,应该能分到一套单元房。
小区是新建的,红砖白瓦,还有统一的煤球房和自来水龙头,在我们那个城市,能住上这样的房子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
可就在分房名单即将公布的前一天,厂里领导的侄子从南方调来,硬是把那套房子给了他。
消息传来时,我们正在吃晚饭,母亲蒸的白面馒头和炖的土豆片肉丝。
"这不公平。"母亲小声说着,眼神担忧地看向哥哥。
哥哥夹了一筷子土豆,慢慢咀嚼着,表情平静得让人心疼:"算了吧,日子还长着呢。"
父亲放下筷子,眼睛瞪得溜圆:"咋就算了?你在厂里干了八年,评过两次先进生产者,凭啥轮不到你?"
哥哥轻叹一口气:"爹,您少操这个心。"
"少操心?你媳妇肚子都有七个月了,再有两个月孩子就出生了,你们还挤在单身宿舍那十来平米的地方,我能不操心吗?"
父亲的筷子在桌上敲出一阵急促的响声,像是他胸腔里那颗焦急的心。
"爹,您消消气。"我赶紧给父亲倒了杯凉白开,"这大热天的,别上火。"
哥哥放下碗,静静地看着父亲:"当年您教我做人,说要忍一时风平浪静,现在怎么自己做不到了?"
"那不一样!"父亲猛地站起来,"我那是教你做人处世的道理,不是让你当窝囊废任人欺负!"
"我不是怕事,是懂事!"哥哥难得提高了嗓门,"您那时候是什么情况,现在又是什么情况?人家有后台,咱能怎么办?"
"那你就甘心让人欺负?"父亲的脸涨得通红。
"我不是窝囊,我只是明白什么仗该打,什么仗不该打!"哥哥把碗重重放在桌上,发出一声脆响。
饭桌上的空气凝固了,连院子里知了的叫声都显得格外刺耳。
就这样,父子俩僵持了三天。
第四天清晨,公鸡刚啼过第一声,哥哥就收拾起行李,说要去新疆建设兵团。
母亲坐在门槛上哭成了泪人:"儿啊,你媳妇都怀着孩子了,你这是要去哪受罪啊?"
嫂子倚在房门上,一言不发,只是用手轻轻抚摸着隆起的腹部,脸色苍白。
父亲却倔强地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吧嗒吧嗒抽旱烟,烟雾缭绕中,他的眼睛像是结了一层霜。
哥哥背着那个军绿色的帆布包,在院子里站了许久,最终走到父亲面前:"爹,我不是跟您赌气,我是想闯出一片天地给您看。"
父亲别过脸去,手指间的烟头明明灭灭。
"新疆缺人手,工资高,一个月能拿六十多块,我省吃俭用,很快就能攒够钱买房子。"哥哥的声音很平静,但我听得出里面压抑的情绪。
"你走吧,想去哪就去哪,别在这晃悠碍眼!"父亲猛吸一口烟,呛得连连咳嗽。
母亲拉着哥哥的手,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个红色的小纸包:"这是娘给你包的护身符,到了那边记得放在枕头底下。"
哥哥接过小纸包,轻轻塞进内衣口袋:"娘,您别担心,我有妹夫的表哥在那边,他说能给我搞个技术岗位,我很快就能站稳脚跟。"
他蹲下身子,握住嫂子的手:"你在家安心养胎,等我安顿好了就接你们过去。"
嫂子点点头,泪水无声地滑落。
哥哥最后看了父亲一眼,父亲依然背对着他,肩膀却微微颤抖着。
此后,只有几封寥寥数语的信寄回家,大多是告诉母亲他平安无事,工作如何如何忙碌,从不提生活有多艰苦。
对父亲,只字未提。
每当母亲读信的时候,父亲总是装作不在意,却把耳朵竖得老高,生怕漏掉一个字。
嫂子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陈小海,意为虽是一滴水,也要汇入大海洋。
哥哥回来看了一次,待了不到三天就匆匆离开,走时依旧没和父亲说一句话,两人同在一个屋檐下,却像是隔着天山。
转眼冬去春来,哥哥的小海都会扶着桌沿蹒跚走路了,却依然不见父子和解的迹象。
直到那年正月初八。
现在,父亲要去新疆了。
我放下手里正在缝补的毛线衣,不解地问:"爹,您怎么突然决定去新疆了?这大冷天的,火车上挤得很。"
父亲将那件半新不旧的棉袄塞进旧皮箱里,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做梦梦见你哥了,站在戈壁滩上,风沙那么大,他都瘦了。"
我愣住了,从来没见过父亲这样。
母亲在灶台边煮饺子,闻言叹了口气,小声对我说:"你爹这一年,天天半夜三更起来看你哥的照片,以为我不知道。前天晚上他又翻出你哥的工作证看,看了半宿,眼睛都红了。"
我这才明白,父亲那坚硬如铁的外壳下,藏着一颗多么柔软的心。
"你哥那个倔脾气,跟你爹一模一样。"母亲继续说,手里的动作没停,"两块硬石头碰在一起,得有一个先软下来。"
饺子的香气弥漫在厨房里,那是哥哥最爱的三鲜馅。
母亲蒸了一笼热气腾腾的馒头,又煮了一大锅饺子,用油纸包好,放在纸盒子里,外面再裹上几层报纸和一条旧毛巾。
"到了地方热一热就能吃,"母亲叮嘱着,眼圈红红的,"你爹从小就不会说那些好听的,你转告你哥,别跟他一般见识。"
寒冬的火车站挤满了回家过年的人,唯独父亲逆着人流去往遥远的西部。
我送他上车,他捧着那个纸包,左看右看生怕压坏了:"这是你妈包的饺子,冻得硬邦邦的。到了地方热一热就能吃,你哥最爱吃你妈包的三鲜馅。"
我注意到父亲的鬓角已经全白了,额头的皱纹也比去年深了许多。
"爹,您路上注意安全,到了给家里打个电话。"我掏出钱包,想给父亲多塞点路费。
父亲却摆摆手:"不用,我有工资,这几年没怎么花钱。"
火车汽笛响起,我不得不离开车厢。
站在月台上,看着车窗里父亲日渐佝偻的背影,我突然意识到,我们的父亲老了。
那个曾经在工厂里扛起两百斤钢材的壮汉,那个在院子里能单手提起我和哥哥的男人,如今也有了不服输的老倔脾气和掩饰不住的柔软心肠。
回家的路上,我经过国营商店,柜台里摆着刚到的收音机,价格不菲,整整一百三十八元。
我想起哥哥离家前说过,想给父亲买个收音机,让他晚上能听听京剧,可惜一直没攒够钱。
父亲去新疆的第三天,母亲坐立不安,一直念叨:"也不知道他们见着面会说些什么,你爹那个人,嘴上没个把门的。"
嫂子抱着小海,轻声安慰她:"娘,您别担心,男人嘛,哪有说不开的事。"
小海咿咿呀呀地学着说话,胖乎乎的小手拍着外婆的脸:"外婆,外婆。"
母亲眼泪都出来了:"这孩子,都会认人了,他爹却还没好好抱过他几次。"
第五天,院子里的喜鹊叫个不停,母亲说这是好兆头。
第七天,大院里的老李头上门拜年,顺便打听父亲的消息:"陈家的老头子真够义气,大冬天的跑那么远找儿子,这年头这样的父亲不多了。"
第十天,依然没有消息。
第十二天,我去邮局询问电报,却被告知没有收到任何来自新疆的电报。
母亲的眼圈一天比一天深,饭也吃不下了,却还逞强说:"你爹向来是有主意的人,不会有事的。"
第十五天,正当我们一家人忧心忡忡地守在电话机旁,盼着有消息传来的时候,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
电话那头嘈杂不堪,父亲的声音断断续续:"找到你哥了……"没等我细问,电话就被挂断了。
那短短的几个字却如同一颗定心丸,让全家人终于松了一口气。
母亲立刻张罗着要准备年货:"你哥肯定要回来过年了,咱得多准备些好吃的。"
直到他们一起回来那天,我才知道事情的全部经过。
父亲到了兵团,发现哥哥住的是集体宿舍,一间屋子挤了八个人。
当时哥哥不在,他的铺位上堆着工具和冻得硬邦邦的工作服,床头钉着一张全家福,照片已经泛黄,却被小心地用透明胶带封了起来。
父亲等了一整天,遇到哥哥的战友李铁生。
"您是陈大哥的父亲?"李铁生一眼认出了父亲,惊讶地问,"您和陈大哥长得真像!他常提起您,说您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
"他过得好吗?"父亲声音发颤,像是怕听到什么不好的消息。
"吃苦耐劳,从不叫苦,团里评过两次先进。去年冬天水管爆裂,他半夜下到冰窟窿里修,差点冻坏了手。现在是技术骨干,刚升了小组长呢!"李铁生说起哥哥,满是敬佩。
"那他为什么不写信回家?"父亲眼睛亮了起来,随即又暗淡下去。
李铁生犹豫了一下:"可能是怕您失望吧。他去年有机会调回内地,条件比这儿好多了,可他没去。"
"为什么不去?"父亲紧紧抓住李铁生的手。
"他说,没做出点成绩,怎么有脸回去见您?还说什么'不摘桃子就别先伸手',我们都不太明白。"
父亲的眼睛湿润了:"这个傻孩子"
原来这句话是父亲年轻时常说的,意思是不劳动就不该享受成果。
李铁生告诉父亲,哥哥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晚上还学技术,就是为了能多挣些钱寄回家。
"他把工资卡都给了他爱人,只留够自己吃饭的钱。"李铁生说,"有一次我们聚餐,他连盘花生米都舍不得点,说要省着花钱。"
父亲在兵团足足等了三天。
第三天傍晚,风沙很大,他裹着军大衣站在宿舍外面,远远看见一个瘦高的身影顶着风走来。
那人穿着厚重的棉工装,帽子上落满了风沙,背影却与年轻时的父亲如出一辙。
"爹?"哥哥认出了父亲,却站在原地没动,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父亲迎上去,嘴唇动了动,却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抖开了冻僵的手指,从怀里掏出那个已经破损的纸包。
"你妈包的饺子,都冻坏了。"父亲的声音哽咽着。

哥哥接过纸包,眼圈红了。
纸包已经在长途颠簸中破损,露出里面冻得硬邦邦的饺子,但那熟悉的形状,那独特的褶皱,无不透露着家的气息。
"爹,您怎么"
"想你了,就来看看。"父亲打断他,声音粗粝如砂石。
两人沉默着走进宿舍,哥哥烧了水,倒了两杯。
父子俩面对面坐着,谁也不说话,茶水的热气在两人之间升腾,模糊了彼此的面容。
"听说你能回内地不回?"最终父亲开了口。
"嗯。"哥哥低着头。
"为啥?"
"我答应过您,要闯出一片天地。"哥哥的声音很轻,"我还没做到。"
父亲沉默了很久,从破旧的皮包里掏出一张照片递给哥哥。
那是全家福,照片已经泛黄,边角都磨圆了。
照片上,穿着新中山装的父亲面容严肃,站在全家人中间,像一棵顶天立地的大树。
哥哥盯着照片看了许久,突然发现父亲的头发已经全白了,脸上的皱纹纵横交错,如同干涸的河床。
"爹"
"人这辈子,"父亲打断他,声音沙哑,"拼命证明自己的时候多了去了,可亲人在一起的日子,经不起耽搁。"
哥哥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
"你妈说,你儿子都会走路了,都会叫外婆了,却还不认识自己的爹。"父亲继续说,"我那天看着院子里老王家的孙子骑在他爹肩膀上,笑得那么开心,心里就想,你儿子啥时候能这样?"
哥哥握紧了茶杯,指节发白。
"你说你要闯出一片天地给我看,可我这把老骨头,还能看多久?"父亲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轻,"我就想,在我还能动的时候,看看你们一家子在一起的样子。"
宿舍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那是时间无情流逝的声音。
"爹,我以为您一直不认可我。"哥哥终于开口,"我以为您觉得我不够强硬,不够有出息。"
父亲苦笑着摇摇头:"我那是心疼你啊,傻孩子。什么房子不房子的,哪有你们一家人在一起重要?"
那天晚上,父子俩聊了很多,从哥哥小时候打碎邻居家玻璃被父亲揍了一顿,到哥哥初中毕业想去当兵被父亲拦下,再到后来进厂工作、结婚生子
宿舍的灯光昏黄,投下两个时而重叠时而分开的影子,仿佛他们这几十年的人生。
第二天一早,哥哥去找了团领导,申请了年假。
"我要回家过年。"他说。
临行前,他把自己攒的钱全部取了出来,整整六百多块,那是他一年多省吃俭用的积蓄。
回程的火车上,父子俩有说有笑,哥哥把这一年来的见闻告诉父亲,父亲则讲述着家里的变化。
"你妈把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下种满了韭菜,说是等你回来包饺子吃。"
"小海长得虎头虎脑的,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就是比你淘气多了。"
"隔壁老张家的闺女考上了师范学院,全院子的人都去喝喜酒了。"
这些家长里短的絮叨,在寒冬的列车上,温暖着两颗曾经疏远的心。
正月十五那天,我正在院子里挂灯笼,忽然听见大门咯吱一声响。
抬头一看,父亲和哥哥肩并肩地站在门口,两人的肩膀上都落了薄薄的一层雪,却都笑得如此灿烂。
"回来啦!"我激动地跑过去。
母亲从厨房跑出来,围裙都来不及解,抹着眼泪喊:"快进来,饺子刚下锅!"
嫂子抱着小海站在堂屋门口,泪光中带着笑意。
小海眨巴着大眼睛,好奇地看着这个陌生又熟悉的男人。
哥哥蹲下身子,张开双臂:"儿子,爸爸回来了。"
小海怯生生地看着哥哥,忽然咧嘴一笑,扑进了父亲的怀抱:"爸爸!"
那一刻,父亲站在一旁,眼中闪烁着晶莹的泪光。
屋里的收音机正播放着新年特别节目,院子里飘着饺子的香气,屋檐下的冰凌在滴水。
父亲拍了拍哥哥的肩膀,语气中充满了欣慰:"咱们陈家的人,就该在一起。"
哥哥点点头,回头看向父亲:"爹,您说得对,人这辈子最重要的不是证明什么,而是和家人在一起。"
窗外,鞭炮声此起彼伏,红灯笼在风中轻轻摇曳,映红了一家人的脸。
北方的冬天再长,也终究会过去。
就像父子之间的隔阂,再深,也终将在亲情的春风里消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