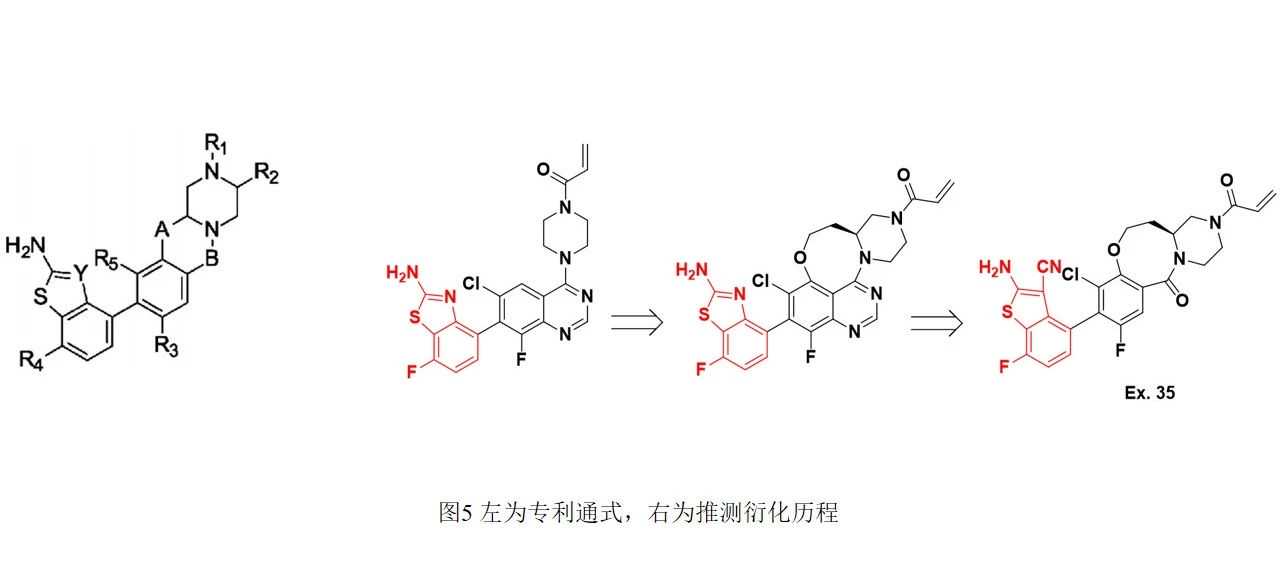"娘家人不给我添菜,丈夫家里的人不给我夹菜,难道我这个新媳妇今天真要饿肚子?"大姑姐高月梅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让满屋子的宾客都听见了。
屋子里的笑声一下子安静下来,只剩下筷子碰盘子的声音。
那是一九九二年初春,我嫁给了高家的小儿子高建国。窗外的杨柳刚刚冒出嫩芽,风里还带着料峭的寒意。
我和建国的婚礼不算大,却也热热闹闹。他们厂里的同事,我罐头厂的工友,两家的亲戚,七八张桌子,坐得满满当当。
建国是知青返城后分配到市里轻工厂的技术员,踏实肯干,人缘也好。厂里分给他一间十多平米的集体宿舍,床、桌、柜,简单得很,却是我们婚后的小天地。
我陈玉兰是城郊村的姑娘,初中毕业就在生产队做活,后来赶上改革开放,到县城罐头厂当了工人。厂里一个月工资七十多块,星期天还能回村里帮家里干活。
我们是通过同事介绍认识的,见面那天,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我穿着姐姐送的花格子衬衫。四目相对,彼此都觉得满意。交往半年便定了亲。
建国的大姑姐高月梅,在区百货公司当营业员,是个说一不二的人物。她从我和建国相亲那天起,眼神里就带着不屑。"一个农村丫头,连高中都没上完,嫁进城里有什么本事?我看是她运气好!"这些话,后来被婆婆悄悄告诉了我。
婚礼那天中午,亲朋满座。高月梅穿着崭新的的确良衬衫,脖子上挂着细细的金项链,手腕上戴着一块上海牌手表,一副城里人的派头。我被灌了几杯橘子汽水,脸红扑扑的,正吃着喜面,就听见她那句话。
"大姑姐,这是怎么了?"建国放下筷子,赶紧问道。他额头上的汗珠在暖气熏蒸的屋子里显得格外明显。
"咱家有规矩,新媳妇得露一手,做道菜给公婆尝尝。我看她是农村姑娘,肯定有手艺,做个'狮子头'试试?"高月梅扬了扬下巴,看了看我穿的红色喜服,嘴角微微上扬。
席间顿时安静下来,连电视机里春晚的重播声都显得刺耳。"狮子头"是我们这一带有名的硬菜,肉馅要拍打得恰到好处,火候掌握得精准,做工复杂。我虽然在家常帮忙做饭,但从没做过这么讲究的菜。
婆婆坐在我身边,拉了拉我的衣袖:"月梅,这哪有这规矩,你别为难人家了。"她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怎么?难道她连这都不会?那我们高家可真是家门不幸啊!"高月梅的话里带着刺,像冬天的北风一样冷。
我握紧了拳头,努力不让眼泪掉下来。建国正要说话,我拦住了他:"我去做。"我放下筷子,抚平红色的新衣襟,朝厨房走去。
厨房里油烟弥漫,灶台上一口大铁锅冒着热气。我翻出家里的肉馅,加入葱姜蒜末,打入鸡蛋,放入水淀粉和料酒,顺着一个方向搅拌。我记得小时候看娘做过,虽然不熟练,但基本步骤还记得。
手上沾满肉馅,我额头渗出细汗,心里紧张得很。厨房的窗户上结了一层薄薄的水雾,映出我有些慌乱的脸。
"需要帮忙吗?"建国悄悄走进厨房,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给我擦汗。
"你先出去吧,我自己来。"我勉强笑了笑,不想让他为难。
"别怕,做不好也没关系。"他握了握我的手,眼睛里满是心疼和歉意。
"快出去吧,别让大姑姐看见。"我小声催促道。
肉馅拍打好后,我开始团肉丸。每一个都要大小均匀,表面光滑,才能入味又好看。锅里的油开始冒烟,我小心翼翼地把肉丸放进去,生怕溅出油来。
炸至金黄后,我又开始炖煮。热气熏得我满脸通红,汗水浸透了新做的发型。我想起小时候,每到过年,娘总会做一大锅红烧肉,那香味能飘满整个村子。现在,我也要用这双手,做出让丈夫家人满意的菜肴。
一个小时后,我端出一盘色泽金黄,冒着热气的狮子头。虽然形状不太完美,大小也不太均匀,但香气四溢,肉质松软。
"来,请厂里的徐厂长先尝尝。"高月梅抢在所有人前面说道,嘴角带着若有若无的笑意。
我这才注意到,角落里坐着一位中年男子,穿着深色的西装,打着领带,是建国厂里的领导。我的手不由得抖了一下,差点打翻了盘子。
徐厂长夹了一块,慢慢品尝。屋子里安静得连呼吸声都能听见。他咀嚼几下,突然眼睛一亮:"这狮子头做得不错啊,肉质松软,味道醇厚,比我们厂食堂的强多了!"
"是啊,玉兰手艺好。"婆婆笑得合不拢嘴,连连给我夹菜,"快吃饭吧,忙活半天了。"
大姑姐的脸色变了几变,端起酒杯敷衍着喝了一口。她没再说什么,但眼睛里的不甘心谁都看得出来。
婚后的日子过得忙忙碌碌。早上六点半起床,煮好稀饭,我和建国一起骑自行车上班。他的厂离我的厂有七八里路,不算近,也不算太远。
"媳妇,你这狮子头真好吃,改天再做呗?"建国常常这么说,眼睛里满是笑意。
我们住的是单位的集体宿舍,两人挤在一张单人床上,床板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房间里只有一张小桌子,一个衣柜,再加上灶台和水池,转身都困难。但我们依然甜蜜,每天下班回来,一起在收音机的伴奏下吃饭聊天。
不久,厂里要分房子,按工龄和职位排序。建国工作四年,正好够条件。那段时间他每天回来都兴奋地讲一些关于新房的事情:"听说是楼房,有独立的厨房和厕所,比我们现在住的强多了。"
婆婆也欣喜地准备给我们添置新家具:"等你们有了新房,我那台缝纫机就送给你们。以后你给建国做衣服就方便了。"
就在公示前一天,高月梅的丈夫张德林找到分房小组的组长——恰好是他的远房亲戚,不知说了些什么。
第二天,建国从厂里回来,脸色不太好看。
"怎么了?"我正在洗菜,看他闷闷不乐的样子。
"玉兰啊,你和建国先缓缓,这批房子技术人员名额有限。"他模仿着组长支支吾吾的样子,"明明昨天我的名字还在名单上,今天突然就没了。"
我放下手中的活,给他倒了杯热水:"没事,我们年轻,等下一批也行。"
"我打听了,是张德林从中作梗。"建国攥紧了拳头,"他和分房组长是亲戚,故意在背后说了咱们坏话。"
"算了,别生气了。"我拍拍他的肩膀,"咱们好好过日子,迟早会有的。"
那天晚上,我下班回来,路过小区门口的空地。那里有几位大妈正在乘凉,嗑着瓜子闲聊。
"听说高建国媳妇是靠运气好才嫁进城的,人家高月梅看不上呢,说是攀高枝。"一位戴着老花镜的大妈说道。
"是啊,我听说这媳妇连高中都没毕业,能嫁个城里人已经不错了,还想分什么房啊?"另一位穿着碎花布衫的大妈接茬道。
"人家月梅说了,弟弟结婚太急,找了个农村姑娘,以后有的后悔呢!"
我站在不远处,脚步顿住了。夕阳的余晖洒在地上,拉长了我的影子,也拉长了心中的难过。我没走过去,而是绕了条远路回家。
建国见我回来晚了,担心地问:"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厂里加班。"我没有告诉他听到的话,不想让他更难过。
春去秋来,我和建国还住在厂里的集体宿舍里,但我们依然过得踏实。我学会了各种省钱的方法,吃饭尽量在家做,衣服能补就不买新的。建国的工资全都上交给我,每个月还能存下一小笔钱。
转机在半年后出现。那天周末,徐厂长来宿舍区视察,正好遇见我在公共厨房做饭。我那天做了红烧茄子和清炒青菜,香味飘了一走廊。
"这不是会做狮子头的小陈吗?"徐厂长笑着打招呼,手里拿着一份文件。
我连忙擦擦手,脸上带着惊讶:"徐厂长好。"
"你这做的什么菜?闻着挺香啊。"他看着锅里的饭菜问道。
"没什么,就是家常菜。"我有些局促地回答。
徐厂长点点头:"我记得你的手艺,那狮子头味道确实不错。对了,厂里新建的职工食堂缺个有手艺的人,你有兴趣吗?"
我愣住了,没想到会有这样的机会:"可是我在罐头厂上班"
"这个好办,两家都是轻工系统的,我和你们厂长是老同学,打个招呼就行。"徐厂长说得轻松,"工资比你现在高两级,还有奖金。"
就这样,我成了职工食堂的炊事员。每天凌晨四点多起床,骑着自行车赶到食堂,开始准备早餐。大锅饭、小菜、稀饭,样样都要照顾到。
起早贪黑,腰酸背痛,但我从不喊苦。冬天的清晨特别难熬,厨房里的自来水冰凉刺骨,我的手冻得通红,裂开了口子。建国心疼地给我买了一瓶雪花膏,每天晚上帮我擦手。
"这工作太累了,要不你还是回罐头厂吧?"他看着我布满冻疮的手说道。
"没事,这里工资高,而且有奖金。"我笑着回答,"再说徐厂长帮了我们这么大忙,不能辜负他的好意。"
手上的冻疮和油烫的疤痕是我的勋章。我用心研究菜谱,变着法子让工人们吃得开心。记得有个老师傅喜欢吃咸一点的,我就专门给他的饭菜多加点酱油;有个女工不爱吃葱,我每次都记得给她的菜里不放葱。
食堂饭菜越来越受欢迎,连附近单位的人都慕名而来。我还根据季节变化调整菜谱,夏天做些清淡爽口的,冬天则做些暖胃的炖菜。每到发工资那天,我还会特意多加几个荤菜,让大家改善生活。
徐厂长经常来食堂吃饭,每次都夸我:"小陈啊,你这手艺是咱们厂的宝贝啊!"
更令人惊喜的是,新一批分房名单上,有了我和建国的名字。那是一套五十平米的两居室,在三楼,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阳台朝南,采光极好。
"玉兰,这都是你的功劳啊!"建国抱着我转了一圈,眼睛里闪着泪光。
婆婆也高兴得不得了,拿出珍藏多年的布料,给我们做了新窗帘:"这是我当年结婚时候的嫁妆,一直舍不得用,现在给你们吧。"
我们搬进新房的那天,院子里的邻居们都来帮忙。有拎包的,有抬家具的,大家说说笑笑,热闹非凡。唯独不见高月梅一家人的身影。
新房里,我把那台缝纫机放在阳台上,阳光照在上面,闪闪发亮。我暗自发誓,一定要好好过日子,证明自己不是靠运气,而是靠实力和勤劳。
日子过得忙碌而充实。我在食堂工作,每天变着花样做菜;下班后还接一些缝补的活,贴补家用。建国也更加努力工作,很快被提拔为车间技术组长。
"玉兰,对不起。"一天下班后,高月梅突然出现在食堂门口,手里提着一包点心。她的头发已经有些花白,脸上的皱纹也比以前多了。"我之前看不起你农村出身,觉得你配不上建国,还处处刁难你。现在我明白了,人贵在有本事,有心。"
我愣住了,没想到这位高傲的大姑姐会来道歉。手上正擦着的碗差点掉在地上。
"大姑姐,过去的事就别提了。"我擦擦手,接过点心。
"不,我得说清楚。你知道吗,现在厂里的人都夸你,说建国找了个好媳妇。连我们商店的同事都羡慕呢,说你做的饭菜特别香。"她的声音有些哽咽,"我我以前太势利了。就因为你是农村姑娘,我就觉得你配不上我弟弟,还让德林去说情,阻止你们分房子。"
窗外飘起小雪,屋内的炉火映红了我们的脸。我沏了杯茶给她,看着茶叶在水中舒展开来。
"大姑姐,我不怪你。"我真诚地说,"我理解你是为了建国好。"
"不,我是自私。"她苦笑着摇摇头,"其实我是嫉妒你。你知道吗,我和德林结婚十年了,家里大事小事都是他做主。他那个人势利眼,见风使舵,我早就看透了。可看到你和建国这么恩爱,我心里不是滋味。"
我没想到高月梅会向我倾诉这些。她一直给人高高在上的感觉,没想到内心也有脆弱和无奈。
"大姑姐,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难处。"我给她递了张纸巾,"建国对我好,我也是用心经营这段感情的。"
她擦擦眼泪:"我今天来,其实还有件事。德林单位最近出了点事,他可能要下岗。我想问问,厂里食堂还缺人手吗?"
我没想到高傲的大姑姐会来找我帮忙。想起她曾经对我的刁难,我本可以拒绝,但看着她焦急的眼神,我鼻子一酸:"我去和徐厂长说说,食堂后厨确实缺个帮工。"
那一刻,隔阂如冰雪般融化。高月梅紧紧握住我的手,眼里含着泪水:"玉兰,谢谢你。"
后来,张德林真的来了食堂工作。刚开始他不习惯,总是抱怨这抱怨那。我没有计较,每天耐心教他切菜、洗碗、打扫卫生。慢慢地,他也融入了这个集体,变得勤快起来。
我和高月梅的关系也越来越好。每逢节假日,我们两家人会一起吃饭,有说有笑。她再也不提"攀高枝"的事,反而经常在亲戚面前夸我能干。
十年后的春节,高家团聚。我已经从食堂的炊事员升为后厨主管,建国也当上了车间主任。我们有了儿子小东,已经上小学三年级,成绩优秀。
饭桌上,我正要下厨,高月梅拦住我:"今天我来露一手。"她笑着从柜子里取出一条新围裙,是农历新年前特意从百货商店买的,鲜红的底色上绣着喜庆的花纹。
她亲手系在我腰间,系得格外仔细:"弟妹,命好是福气,但真正让人佩服的是你这十年的付出。记得你刚嫁进来那天,我让你做狮子头刁难你,没想到反而成了你的转机。"
我笑着握住她的手:"大姑姐,没有你的那次'刁难',我可能到现在还在罐头厂做工人呢。"
"哎呀,你就别安慰我了。"她不好意思地摆摆手,"还记得那天我去食堂找你道歉,你二话不说就帮了我家德林。那时候我才真正明白,什么是善良和宽容。"
厨房里,我们俩一个和面,一个切菜,配合得熟练而默契。窗外,雪停了,阳光透过玻璃洒在地上,照出一片明亮。院子里,小东和表哥在堆雪人,欢声笑语飘进厨房。
"大姑姐,你看."我指着窗外,两个孩子正在追逐嬉闹,"这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
"是啊。"她点点头,眼里闪着泪光,"以前我总觉得门户很重要,城里人就比农村人高一等。现在想想,真是愚蠢。人活一辈子,家和万事兴,这才是最珍贵的。"
锅里的狮子头冒着热气,香味弥漫了整个家。我和大姑姐并肩站在灶台前,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地上,温暖而明亮。
"来,尝尝我的手艺。"她盛了一碗汤给我,"学了你这么多年,不知道有没有进步。"
我尝了一口,点点头:"比我做的还香呢!"
"少来!"她笑着打了我一下,"你这张嘴啊,就会哄人开心。"
厨房的门被推开,建国探头进来:"怎么样,两位大厨,饭菜好了没?我们都饿了!"
"马上就好!"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然后相视一笑。
阳光从窗户洒进来,照在缝纫机上,闪闪发光。那台缝纫机已经陪伴我十多年了,缝过冬衣夏裳,也缝合了曾经的隔阂和误解。现在,它静静地见证着我们家的幸福与和睦。
院子里,雪人已经堆好了,戴着建国的旧帽子,插着一根胡萝卜当鼻子,憨态可掬。孩子们围着它拍照,笑声清脆。雪人旁边,是我们的故事,是这个平凡却温暖的家。
门外,鞭炮声此起彼伏,迎接新的一年。我知道,无论前方有什么,我们都会一起面对,就像当年那道狮子头一样,用心做好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