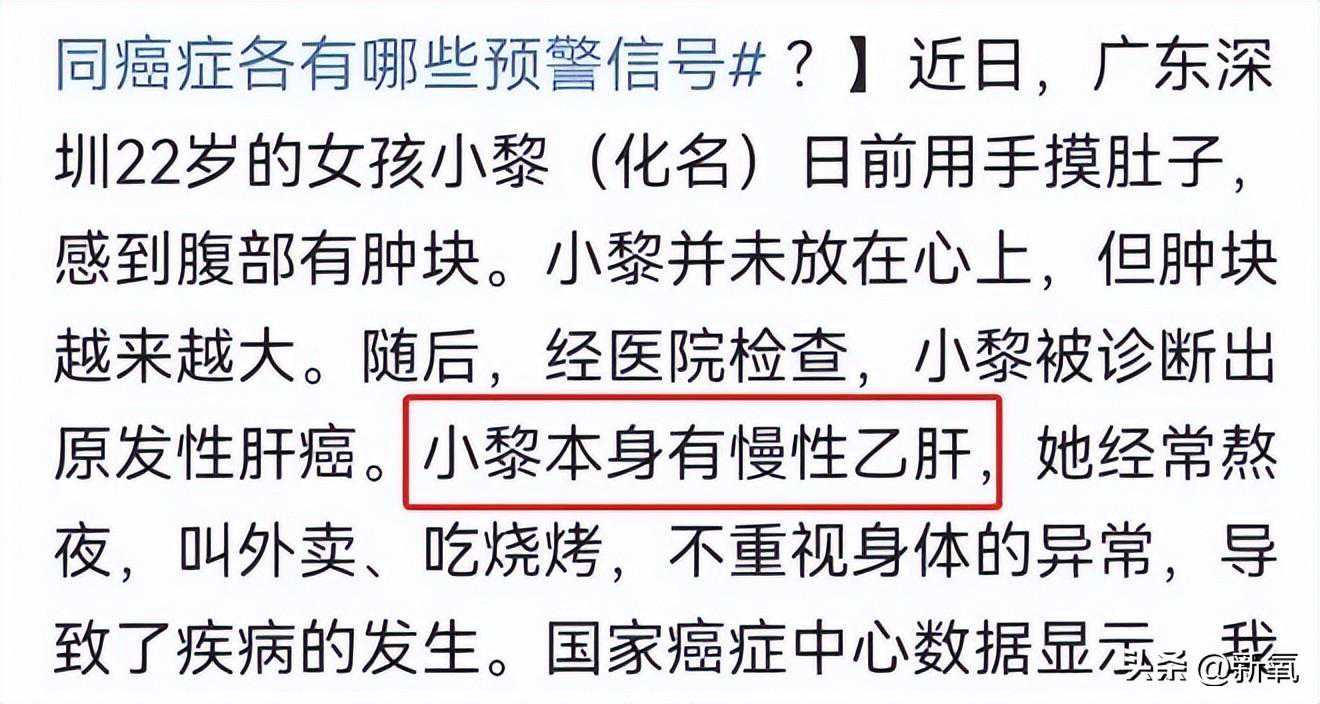“人生不如一句波德莱尔”。对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一般印象,我们停留在《恶之花》里那些腐败而唯美的意象:疯狂的赌徒、美丽的盲女、清冽的月光、恐怖的腐尸。这位晚期资本主义的抒情诗人敏锐地捕捉到了第二帝国时代的巴黎所弥漫的颓废情绪与时代精神,并以他的天赋进行了表达。他是自我放逐的流浪者,也是真正的先知:他看到了城市的暧昧与现代文明的压抑,也洞悉到存在于每个人身上的孤独。
19世纪的巴黎街头
然而对于波德莱尔本身,我们却知之甚少。在好友戈蒂埃的《回忆波德莱尔》中,这位诗人“有自己的王国,自己的臣民,自己珍贵的创造物。”同样,究竟是什么孕育了这位离经叛道的诗人,而群星灿烂的十九世纪又是如何塑造了波德莱尔独特的美学观念?阅读法国文学研究者克洛德·皮舒瓦和让·齐格勒合著的《波德莱尔传》也许会带给我们新的感受,也许我们印象中离经叛道的现代派诗人,其实有着与普通人相似的自负与虚荣心。同样,深深地介入时代并被时代形塑的诗人并非觉得自己是现代派的开宗立派之人。他更希望诗人们能够看到工业化的灰霾天空下,工人们的“领带与上了油的靴子”。然而正是这样的洞见,使他预见了未来的时代所弥漫的现代情绪:在都市生活的孤独与碎屑中,在被现代性所规训的心灵中,寻找其中残存的诗意。
《波德莱尔传》[法]克洛德·皮舒瓦、让·齐格勒/著董强/译商务印书馆2025年11月
波德莱尔的“阴暗面”
波德莱尔墓地上的雕像
但真的有必要花费如此的篇幅去考证“参议院秘书长”波德莱尔先生,和孤女波德莱尔太太的族谱么?真的有必要让一个对波德莱尔感兴趣而打开这本七百多页厚书的读者,先从波德莱尔这个词到底该怎么拼,迪-法伊斯太太到底是不是真的和迪-法伊斯先生结了婚,迪-法伊斯先生到底是不是参加了保王军写起么?
《恶之花》[法]波德莱尔著钱春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4月
孕育诗人的“腐朽”家庭

龚古尔兄弟
波德莱尔比普鲁斯特早出生半个世纪,他生活的年代里圣伯夫的方法是文学界造星的主流手段。波德莱尔一生都和圣伯夫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非常清楚人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诗人。所以他绝不会像普鲁斯特那样说“小说里的那个马塞尔不是我!”甚至,他还会亲自演示一个诗人到底该怎么去写一本诗人传!波德莱尔的代表作《恶之花》本身就是一部诗人传记,唯一贯穿始终的主角就是“诗人”。诗集伊始,诗人诞生在一个充满了“衰朽文明的家庭”,摇篮边满是“拉丁灰烬”。他从小浸染在这衰朽帝国的颓废趣味里,在孩童的年龄就已经在精神上衰老了。他有一个同样衰老的父亲,和一个诅咒他的母亲。他离开了家庭却陷入现代生活的深渊不能自拔。被堕落的罪恶诱惑,被冷酷的世界折磨,寄希望于灵魂的救赎却找不到可以依靠的信仰,内心想要祈祷嘴里吐出来的却是“念给撒旦的连祷文”。
但假如不止步于感动,而是产生了一点怀疑,那么这两位几乎把半生的时间都花在波德莱尔身上的研究者用这本《波德莱尔传》给出了答案。
浪漫主义诗人的判决
1857年《恶之花》受审,圣伯夫为波德莱尔辩护的理由是“这些主题其实缪塞都写过!”“为什么缪塞被选入法兰西学院却要控告波德莱尔?”对这种辩护,波德莱尔自己非常不以为然,因为波德莱尔最看不起的诗人就是缪塞,此外波德莱尔和缪塞都不觉得雨果能算是诗人。
法国诗人缪塞
《巴黎的忧郁》[法]夏尔·波德莱尔著郭宏安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6月
如果连波德莱尔的母亲和母亲的继承人都能在法庭推翻他欠下的最大一笔债务,为什么波德莱尔自己不能呢?更何况他还有一个法庭给他设置的“监护人”昂塞尔。昂塞尔虽然被波德莱尔描述得冷酷又残忍,但事实上昂塞尔对波德莱尔也抱着一种近乎父爱的情感。如果波德莱尔向他求助,奥皮克夫人都能做到的事他也不难做到。再考虑到波德莱尔的亲哥哥就是法官,他亲生父母、继父的家族全是搞法律的,耳濡目染的波德莱尔不会对法律一窍不通。波德莱尔如果向哥哥阿尔方斯诉苦,哥哥只要稍微审查他的账务,就会提示他这笔账不一定成立,到法院去申请就能否决掉。
即使波德莱尔真的负债累累无力偿还,透过本书也可以看到他其实并不像自己说的那么孤立无援。波德莱尔一生都在抱怨可怕的奥皮克将军把他逐出家门,母亲的改嫁剥夺了他幸福的童年。但事实上书中随处可见他写给母亲的求援信,类似“你今天去银行给我汇五十法郎,把汇票塞在信封里寄到…”。纵然奥皮克将军在余生都没有和继子和解,但他终究死在1857年,波德莱尔人生的最后十年里,他又得到了自己的母亲。而且奥皮克夫人一直希望唯一的儿子波德莱尔能够离开巴黎,到翁弗勒尔和自己一起生活。假设一下,波德莱尔真的抛下了他在巴黎的“堕落生活”。到外省和母亲一起生活,用自己的写作还债、靠母亲的钱生活,那波德莱尔会是什么样子?对此有一个最好的参照物,那就是文学宅福楼拜,而且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恶之花》同一年被帝国的轻罪法庭认定为“伤风败俗”。
终究波德莱尔既没有推翻他的债,也没有抛下他在巴黎的生活,到他心心念念的翁弗勒尔的妈妈身边去当另一个福楼拜。因为在巴黎有他想要探索的生活,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的超级大都市巴黎正在冉冉上升。他离不开这个城市、也离不开他日新月异的生活。他甚至离不开那些“每年会苏醒一次”的债主,他需要他们来和自己一起演好“现代生活的诗人”这出戏。
波德莱尔以一种小布尔乔亚的精明态度,走完了诗人那条“通向星星的路”。让同样精明狡猾的纳达尔赞叹不已。在浪漫主义的黄昏,响起了当时还没有名字的“唯美主义”运动的第一声霹雳。而这个神奇且浪漫的故事,在《恶之花》里不会有。在大多数其实大同小异的波德莱尔传记里也不会有。因为它太难写,也太难取悦读者,因为它只有像本书一样被写成一本“审讯记录”,才能被成功的展现。
文/高林
校对/柳宝庆